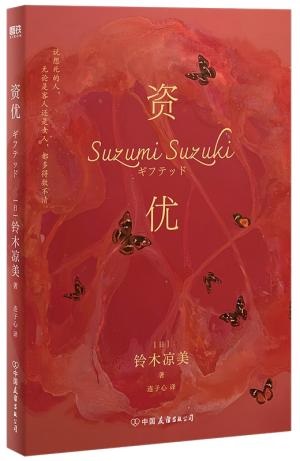{{ _getLangText("m_detailIntroduction_goodsIntroductionText") }}
我所在的街道夜晚嘈雜,可白天幾乎聽不到人的聲音。 這裡是娛樂街,這裡是夜的世界。 在娛樂街,很多人沒有該有的東西——牙齒、睡眠或是夢想,在娛樂街,隨身攜帶裝有兩百萬日元信封的女人多得數不清,和說要去死的女人數量大致相當。 我從十七歲離開家,以處女之身就職於酒吧,從此,喝酒就成了我的工作,每天有一半時間我都在模糊的記憶中度過,另一半時間在幾乎消失的記憶中度過。 這麼多年來,我周圍總有朋友想證明自己與其他人並非處於相同的立場。 至於她們究竟想向誰證明,是個謎,也許是想向自己證明吧。 然而,不幸的是我們全都處在同樣的立場上,沒有一毫米的距離。 世界上有價值高的人,也有價值低的人,而我們這些聚集在這裡的人完全一樣,也許比世界上的其他人更低。
今年夏天,我失去了兩位朋友。 其中一個人已經在五年前結了婚、生了孩子,可她卻和一個男人跑了,失去了聯繫。 她是我中學時的同班同學,她堅持不懈地與當時只顧著和娛樂街的人廝混的我保持聯繫。 我們斷斷續續地聯繫著,然而,當有一天她不再回復資訊,過了一段時間我甚至無法給她發送信息的時候,我接到了她丈夫的電話,這才得知常常莫名其妙晚歸的她終於在某一天沒再回家。 他問我她去了哪裡,可我也不知道。 另一個人則從大阪的出租公寓里一躍而下,離開了這個世界。 我在葬禮上確認了她的屍體,因此至少我知道她去了哪裡。
也許是因為在夏天失去了太多,我欣然地接受了多年未聯繫的母親深秋之前想搬來我家的請求。 母親胃裡的病灶終於到了難以維持生命的地步,她似乎在尋找一個死亡之地。 此刻,陪媽媽一起等待死亡之際,向來沉默的我突然想要問問她:“為什麼我沒有父親?”“為什麼無論我吸煙或是喝酒你都不生氣?”“你知道我在這條街上做什麼工作嗎?”“我撒的謊你知道了嗎?”“為什麼沒打過我也沒拋棄我的你卻燒傷了我的皮膚?”還有“你慶幸生下我嗎?”